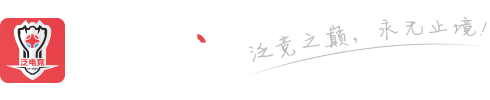
时间:2023-03-19作者:佚名

春天,北三跳(跳海酒馆北京三店)的自动贩卖机上布满客人留下的涂鸦,还有人在玻璃门上印满唇印,鼎盛得像王尔德在巴黎拉雪兹公墓的墓地。
夜晚,诗歌占领酒馆。唯一的空隙留给了舞台,每个人都可以上去读一首诗。外围是黑压压的人群,他们年轻、拥挤、微醺,像一群北方天空中离群的乌鸦。
墙面上挂着黄曜烯的画作。黄曜烯30岁,给自己的名号是“野生艺术学徒”。她热爱画画,在大厂工作了十几年,终于考到了美国的一家艺术院校,准备重启自己的人生。
妇女节那天,跳海北京负责人疼疼和黄曜烯商量出一个创意:复刻她的一幅展现女性身体的画作,并把中国汉字里所有带女字旁的字的女字旁剪掉,让大家自发地把另一半贴到那幅画上。以此为契机,完成又一次客人和跳海的共创。
比起酒馆,跳海更像是一家内容公司。疼疼告诉我,北京的5家店,每年大约会产生200场活动。特别的是,每家门店都有自己独特的定位,会设计出不同的活动。社交媒体上,跳海成了“城市年轻人的庇护所”“互联网人收容所”,年轻人们因为活动慕名而来,并形成了在这里喝酒与交谈的习惯。
酒吧业态在中国,市场格局极度分散,几乎95%的玩家都是独立酒馆。按2020年收入统计,中国酒馆行业CR5仅为2.2%(注:CR5,即业务规模前五名的公司所占的市场份额)。疫情期间生长出来的跳海,已经在全国开出12家门店,并有多家正在筹备中,连锁之势只增不减。
跳海创始人梁二狗曾经表示,跳海的坪效高于奈雪的茶,低于喜茶。跳海合伙人随易给我的客流量数据是,跳海village(俗称北四跳,室内外面积450㎡)全年月均客流量在10000左右(仅夜间),杭州跳海(室内营业面积120㎡)全年月均客流7000左右(仅夜间,仅开业半年样本量)。
曾经有媒体计算过武汉新天地“海伦司 越”的客流量,这家450㎡的门店如果想要盈利,其月平均需达到2700人左右(根据华泰证券研报数据计算)。
海伦司上市后,投资人恍然大悟,一窝蜂地看起小酒馆赛道。当时,跳海在北京只有一家后海老店,不到50平米,墙皮都是脱落的,生意倒是好到出奇,好到让投资人们蜂拥而至。来到店里的投资人一致认为那家店“太鼓楼了”“太小众了”,很难复制。
广科咨询首席策略师沈萌曾对三亿世代表示,小酒馆模式就像餐厅一样,更依赖经营者,优势是可以更精准的为消费者提供有差别的定制服务,劣势是这种模式的经营成本无法形成规模化效应,也很难大规模无损复制。
疫情中,跳海开始向不同城市拓展,同时增加一座城市内的店面密度。“北京的5家门店显然还没有达到密度上限。“梁二狗告诉我,他目前对跳海的预期是全国开到100家以上,“北京至少可以做20家,北上广深基本可以有七八十家,其他城市加起来再有50家,所以100~120家之间是一个目前能预见的状态。”
小酒馆赛道遇到疫情重创。今年2月28日晚,“酒馆第一股”海伦司发布盈利预警,预期2022年收入约15.49亿-15.89亿元,较上年同期的18.36亿元减少约13%-16%;净亏约13.13亿-16.73亿元。去年,海伦司试图加入烧烤盘活生意,收效甚微。
二狗和随易都曾参与风靡一时的社交活动平台Someet创业,二狗也曾说过,跳海就像是线下版的Someet。它们身上都带着那种理想化的、对陌生人友谊乌托邦式的幻想。Someet最终因为商业变现受困于2020年关闭,而跳海目前大部分收入来自酒水营收,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商业化的问题。
我们往往认为商业模式是计划出来的,完整的,规则的,无限趋向于机器与数字的,可复制的;但跳海是野生的,与人紧密相关的,反直觉的,很难大规模复制的。在和梁二狗、随易、跳海北京主理人疼疼、店员面面的对话中,这种矛盾感在我脑海中扩大了。跳海目前的成就是反商业直觉的,在它的持续扩张中,某种矛盾必将生长出来,并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。
如果跳海最终延续了自己制造财富的能力,并且保留了目前的调性与风格,那么它的多元文化、人与人之间的联系,将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商业线索。如果跳海最终费尽力气也没能迈过那个阶段,回到了小而美的状态下,那么那些它引以为豪的那些特质,就将是其没能成为一个商业帝国的最本质原因。
这篇文章要做的,是剥丝抽茧,解构这家起源于二狗家客厅的酒馆,如何成长为今天的规模。他们“反商业直觉”的成长背后,有哪些看似轻巧但深思熟虑的设计,以及那些会阻碍他们继续成长的隐患。
做酒馆界的lululemon
当互联网公司为单个项目开八百个无限内耗的会议时,大量拍脑袋决定的活动ideas在跳海投入运作。
“比起一家酒吧,我们更像是内容公司。”疼疼说,在跳海,对话的核心永远不是哪款酒卖得更好,而是什么创意更好玩。酒、人、社群、空间,所有和跳海产生连接的object,都会成为内容生产的源头。

所有跳海员工都可以是活动发起人,单家店面的活动拍板权在店长手里,不需要经过公司层面。多数情况下,创意都是聊天聊出来的。店员和客人聊天、和店长聊天,出来一个idea,当即就会确定活动时间,梳理活动步骤,立马推进。一个活动最快当天就可以落地。
疼疼和大伙去酒馆门口抽烟的时候,发现不管是谁的打火机,只要在陌生人手里递一圈,总会走上失踪的道路,仿佛比人更能在这个世界上遨游。
于是,他们当机立断,直接去便利店买了100个打火机,打印出100个二维码,一群人围在店里挨个给打火机贴上二维码。扫描二维码,你会看到三个问题:你是谁?你在哪儿?你身边有什么?回答完之后,你还可以看到这个火机每一任拥有者的答案。
这些贴着跳海二维码的打火机们,以跳海为起点,进入一场无尽的漂流。他们散布在街边,出现在外卖袋里,随着主人更迭,在城市间流窜。
这样的小创意、小活动,像翻涌的热带鱼群一样不断在跳海密密涌现着。以北京的5家门店为例,一年大约有200场大大小小的活动,归属于10个左右大IP底下。这些活动有80%的损耗率,举办时不温不火,后续也不再重复,20%效果好的活动会保留下来,一再被客人们期待与参与。
跳海有很多经典活动IP,比如说为社恐人士设计的“默酒”。来店里参加活动的客人会被随机两两分为一组,面对面坐着喝酒。过程中,两人不说话,只能通过纸笔交流。
其中一人先行离开时,可以选择在纸上写下或不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。留在座位上的客人,在对方离开后,如果看到了联系方式,也可以选择是否和对方保持联系。
很多新加入跳海的员工习惯性地想重现这些经典IP,但跳海希望每个人为这里带来不同的东西。更有趣的事,很多灵感都脱离了店员的原有职业。一位在影视行业工作七八年的女孩入职跳海后,举办的第一场活动,是跳舞party。这个曾经点亮了她休息时间的爱好,在跳海生长出了新的可能。
和跳海聊的那几天,我和同事正在为一档节目的改名绞尽脑汁,我们起出了四百多个名字,穷尽了所有元素和组合。“创意”听起来已经不再是鲜活多汁的状态,它不再能燃起我们的热情,而更接近于枯槁。
因此,跳海的行事果决令我感到诧异:较低的决策成本让他们能够迅速拍板,迅速试错。他们不纠结,不内耗,雷厉风行,趣味横生。
更多内容生长于社群当中:客人们共创的美食地图、客人二创的打酒师海报、店里的展览等。二狗希望跳海成为一片土壤,在这里,每个人都可以创造,每个人都是跳海的主人。“后来我们发现,有个牌子叫lululemon也在做一样的事。”二狗笑着说,后来他也向lululemon学习了很多。
他们没有忘记商业化的一面。“不如寻朋友”的诗歌活动安排在周五,周五自然客流量本来就大,这下更是剧增,到达峰值后无法再承载更多客流。复盘中,他们决定未来将类似活动安排在周中,不仅能让客人有更好的体验,也能提振周中的客流量。
深圳跳海的“极限加班一小时”活动安排在每周一,方便大家加班完扔掉电脑就能喝酒;“默酒”往往在周二,也是出于同样的客流量考量。
“先有人才有店。”
跳海3年内开出了6城12家门店,且恰逢疫情期间。外界有很多声音觉得这样过于冒进,但随易觉得这个速度很稳健。他们开店的前提是,在一个城市找到合适的负责人,再开店。这样做的优势是保证跳海的调性,而代价则是对扩张速度有一定的局限。
“人人都问什么时候开武汉店,长沙店。”二狗对我说,“我们也知道武汉好啊,我们特别想开,但是没找到合适的人。”实体餐饮有周期性,如果不能赶在旺季夏季前完成3个月左右的选址、装修、开业,可能就会错过一整年的机会。
在跳海的全国体系里,店铺运营占40人;市场新媒体部门有3位全职员工和1位实习生,除此之外,每个城市有一位兼着市场新媒体角色的人;在深圳的合伙人阿浩带领着一个供应链团队。跳海有大量兼职“打酒师”,每家店铺只有2位全职员工,因此人效较高。
跳海的第一家店实际上是二狗家的客厅,他在家里接了三个酒头,呼朋唤友,大家聚在一起喝酒、听音乐、看电影、聊闲篇,喝多了一开心就跳进后海。从那之后,二狗坚信“人”和圈子的能量。
跳海几十人的团队中,仅两位有实体餐饮经验。二狗做过在线旅游,做过科技公司;疼疼学法律,曾经是公路旅行的嬉皮士;北四跳店长卓越曾经在单向空间工作,给自己的title是“过气网红,落魄主播,新晋恋综嘉宾,小宇宙热搜艺人”;杭州跳海店长以前是编剧;北二跳店员面面教过吉他、滑板,也卖过雪板……
毫无规律可循的人员构成中,有两条直觉性的标准。随易想了半天,告诉我是“nice”且“酷”。
Nice代表了跳海的人情味。疼疼向我描述了一个场景,在很多酒吧的吧台,客人明明就坐在bartender对面,但店员会让客人扫码点酒。这个场景熟悉得让人哑然失笑。跳海的规矩是,吧台里永远要有半个闲人,随时抬头关注客人们的需求。在跳海工作的人,不管性格外向还是孤僻,首先是善良、随时愿意帮助
别人的。
作者黄瓜汽水告诉我,在其他酒吧,去了就是沉默点酒、喝酒。去跳海的时候,会有人开心地给她介绍酒的酸甜度。这看似是服务业的基本操作,实际上却逐渐堙灭在多数大城市的吧台后。
“酷”的意味很丰富,但指向很明确。疼疼说,如果自己不在跳海的商业环境下做各种有创意和个性的表达,他个人也会做。那些反抗、人与人的连接,是生长在他生命里的一部分。跳海店员大多如此。
过去一年,疼疼面试了200多人,面试者来自各行各业。他慢慢发现,大厂员工往往会在面试环节被他刷掉,哪怕进入跳海团队,也很难适应。“他们的工作太模式化了。”适应了螺丝钉式的定位,大厂员工们很难再生长出张牙舞爪的创意,也时常批判跳海“野生”的行事风格。
气场合拍的人进入跳海后,会被予以极大的包容。卓越刚开始管理北四跳(跳海Village)的时候,店面运营做得一塌糊涂。北四跳占地450平米,有铺满鹅卵石的大院子、帐篷,还有红泥小火炉,是名副其实的village。
这里承接了巨大的流量,没有实体餐饮经验的的文化人卓越,完全乱了手脚。跳海村开业2个月时,在大众点评收到了342条评价,其中有14条差评,是北京几家店里占比最高的。卓越擅长的是链接文艺界人士,组织活动。面对客人对服务纰漏的不满,他满是知识分子的清高。

跳海内部把这些差评捋了捋,和卓越一起复盘,帮他提升店铺运营的能力。于是,“我们只招待朋友,我们不服务上帝”渐渐有了补充,即不服务上帝的意思是鼓励客人来跳海当家作主。“本店允许客人自己服务自己,别跟我们客气!”

跳海给员工开工资很慷慨。有员工第一次收到出乎意料的工资时,慨叹道:“我在前司待了那么多年,做一个30万的项目只有1000块提成。”
聊到这段的时候,我和疼疼坐在北二跳震耳欲聋的音响边,他平静又温和地说,能用钱表达的支持,就不需要再作过多的拉扯和交流,“因为大家需要生活”。
非标VS个性化
跳海遇到的最大阻碍就是非标问题。
作为一家早期不强调标准化的品牌,跳海希望能“对症下药”地融入每座城市年轻人的生活。拓店时,二狗发现每座城市的表达有着巨大差异。虽然同样有大量互联网公司存在,北京青年文化的主流是对社会议题和商业议题的积极反思,而深圳年轻人对抗的是“996”“内卷”和“搞钱文化”,二者对每个议题的感知力是不一样的。
在成都、重庆,大家活得很好,没有什么需要对抗的东西,也不需要过多的反思。所以在这两地的跳海,提出的形而上的讨论和表达相对少很多。跳海尝试把每座城市年轻人的“脉”,他们每天是怎么生活的,每天关心的话题是什么?
社群是“把脉”的解决方案之一。跳海上海店还没开业,已经有了自己的几百人社群,聚集了很多领域有能力的人。随易对能量的定义是,未来能和跳海产生一些好玩合作的人,比如文化类app创始人、咖啡厅主理人、潮牌设计师、博主等等。
先拉预热群,是跳海新店开张SOP的一部分。“就连给新店选马桶,我都会扔到群里,先问大家喜欢还是不喜欢。”连装修还没完成,这座城市里的人就已经和跳海的空间发生了关系,成为了共创者。
在这样的预热下,跳海往往开业当天就爆火,并在一到两个月内达到流水天花板。自此,跳海对店铺后期的运营有了基准线。
连锁的标准化意味着同质化。对跳海这样标榜创意的商家来说,“自我复制”不是一个好词。因此,新开一家店的时候,跳海会让新店像一个孩子一样生长一段时间,再找一个柔和的接口,把跳海的特质嫁接进去。
因此,每座城市的每家跳海,都有了自己的个性。比如说,有人反馈,跳海杭州店有点“亚”,和跳海以往的风格不太一样。“亚文化的圈子是封闭的,但跳海的社群是开放的。”随易觉得只要杭州跳海不排外,不局限在“亚”里,就没关系。
在和跳海聊的过程中,我不断思考:很多时候,我们默认,越好玩的东西越不挣钱,越有人情味的生意越难成气候。那么多把开酒吧、开书店、开花店当成人生小目标的人当中,为什么二狗这一批,把梦想做成了赚钱的生意?
跳海每周一开周会,分析流水、客流量、各个平台能拿到的所有数据,做舆情监测,把控利润。他们根据这几年的经验,做了一套公式,从一周酒水销量数据计算出成本,精确到每一桶、每一杯。
一位北京的互联网从业者告诉我,他从不关心跳海的表达,只是觉得跳海地方大,有地方坐,酒不难喝,于是常去。一位杭州朋友告诉我,杭州跳海是她的快乐老家,她每周都要去一两次,但她并没有加入跳海的社群,也没有参加过跳海的活动。疼疼也说,如果硬要他说,其实80%的客人并不是冲着跳海的内容来的。
夜晚的北四跳,一对情侣依偎在一起,轻声细语,试图解出跳海报纸上刊登的谜题。那是一些和跳海有关的纪念日和专有名词。随易看着灯光幽暗下的他们,心中默想,他们成为了跳海的又一枚纪念。